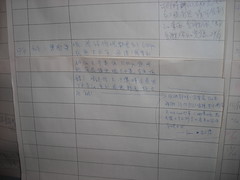如果我的論文中出現的歐化句子是閱讀太多所致,這本書一定功不可沒。
監考期間,同學的手指在鍵盤上風馳電掣,我也幻想自己不如也做做論文。外型美觀的Dell電腦,flash不夠update玩不到travellers’ IQ、經常無故彈出叫人安裝Traditional Chinese package的視窗已經夠煩,重重玩樂的障礙令我終於收下心來開啟論文的檔案,結果這部偉大的電腦偉大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,連手指也detect不到。實在太可怕,這就是廿一世紀的電腦,這就是廿一世紀的Windows XP(其實我唔知關唔關事)。究竟它是政政系派來拯救各位未畢業的研究生,協助他們消除雜念趕快完成論文的救星,還是一條只懂得打擊眾人僅餘工作意志的廢柴?
這部電腦對我而言,明顯就是一條廢柴。所以,唯有繼續閱讀歐化句子。直到今天我終於明白我的論文對老細而言是幾難頂了,真想把書逐頁逐句打交叉呀。
監考期間,同學的手指在鍵盤上風馳電掣,我也幻想自己不如也做做論文。外型美觀的Dell電腦,flash不夠update玩不到travellers’ IQ、經常無故彈出叫人安裝Traditional Chinese package的視窗已經夠煩,重重玩樂的障礙令我終於收下心來開啟論文的檔案,結果這部偉大的電腦偉大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,連手指也detect不到。實在太可怕,這就是廿一世紀的電腦,這就是廿一世紀的Windows XP(其實我唔知關唔關事)。究竟它是政政系派來拯救各位未畢業的研究生,協助他們消除雜念趕快完成論文的救星,還是一條只懂得打擊眾人僅餘工作意志的廢柴?
這部電腦對我而言,明顯就是一條廢柴。所以,唯有繼續閱讀歐化句子。直到今天我終於明白我的論文對老細而言是幾難頂了,真想把書逐頁逐句打交叉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