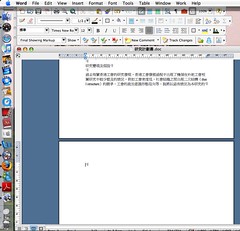星期三, 11月 28, 2007
星期一, 11月 26, 2007
星期二, 11月 20, 2007
南道的盲點

深夜,與李同學在廿四小時麥記吹水,並欣賞其兩年前的歐遊照片。翻看那些故作日常的照片實在饒有趣味,其中一張本來打算拍他那身穿小背心的同行者的背影,但他卻到現在才發現,一位意外入鏡的嬉皮阿叔,在快門閃動的一剎那,向他豎起了兩隻中指。那時,覺得自己的觀察力從來沒有如此好過,實在見笑了。
走出麥記已是一時,想起第二天早上有約,就想馬上回家撲上床呼呼大睡。麥記門口的右側有一暗角位,日間的時候,常有路人在此抽煙,或站在垃圾桶旁吃漢堡包。我們路過的時候,卻看見一個人蜷縮在地上,像是失去知覺,而另一人則站在他的身後,翻著一個類似銀包的物體。
我們和那人交換了一個疑惑的眼神,也沒有停下來,但走遠了五六米後,我問李同學,那人像打劫嗎,而李同學也深有同感。那人究竟是睡著了、喝醉了,還是被襲倒下了?我們向前再走了一兩米才敢回頭再看站著那人,只見他的站姿維持了好久,手的動作也沒有停下來。及後又有兩個年青人從麥記裡走出來,也是疑惑地看著那兩人,然後路過離去。
李同學忽發奇想,難道那人是相信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嗎?可能那人就是覺得,沒有人會相信有人會在麥記門外打劫,所以才大模斯樣地翻銀包,反正大家都不會理會。我們想過報警,但萬一警察要我們協助調查,那就可能要折騰好一陣子了。於是,我們走向最近的屋村電梯大堂,向當值的保安阿姐求助。
我們站在馬路上,向大廈裡的保安阿姐揮手,示意她出來,和我們一起遙遠觀察那兩人。三人就這樣站在行人路的正中間,看著那兩人的背影。起初阿姐不置可否,說這一帶的醉酒佬多的是,常有人喝醉了就直接躺在路上呼呼大睡。我們說,如果那人喝醉了酒,而站著那人又認識他的話,不是應該想辦法送他回家嗎?為何還施施然的在路邊翻著有的沒的?阿姐好像有些動搖,又提出「就算識得都唔應該立亂睇人銀包」,關乎私穩的論點。但她說自己不能擅自離開大廈範圍,於是建議我們報警。「偶然做下好市民都幾好架。」
沒有報警經驗的我們呆了一陣。李同學可能是因為緊張,我是因為眼訓。最後我以電話沒電為由,逼使李同學第一次撥出那熟悉又陌生的九九九。
「喂,我們在樂富間麥記出門見到有個人o係地下暈左,隔離個人揭緊佢銀包喎……下,企o係度個人著藍色風褸架囉……幾高?中等身材卦……呢條咩街?我都唔知喎,麥記果條街囉,宏順樓出面呀……係呀成個樂富得一間麥記架咋!……哦,原來呢條街叫橫頭磡南道呀……警察宜家會黎呀?好呀好呀……下我地要等埋警察來到先走得嗎?好啦好啦……」他放下電話後大約十秒左右,就看到一架警車在身邊掠過。我們驚呼「唔係咁快呀嘛」,但那架警車並沒有停下來。阿姐氣定神閒的說,那警車應剛剛才收到訊息,要多繞一個圈才會停。
果然,警車又從另一個方向駛過來了。身穿藍色風褸的人馬上調整站姿背靠牆壁,這令我們更肯定,他真是有點古怪。我們在遠處看到那人被查身份證,又被盤問了一兩分鐘。我們一方面怕要協助調查,另一方面又八卦,所以還是留下來繼續偷看。
其中一個警察站到一旁,致電李同學。李同學對他說:「其實我o係你後面架咋!」並向他揮手。警察說,原來他倆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,上司喝醉了,倒在路旁,下屬想送他回家,才嘗試看看他的銀包裡面有否其家人的聯絡方法。李同學對警察覆述我們剛才的討論,但似乎就已超出了警察希望知道的範圍。「得喇!交俾我地得架喇!」警察留下豪情壯語,就回到暗角處。我們回去向阿姐交代事情的發展,她說,係囉,警察咪可以幫佢搵到屋企人囉。
大家想像中的驚險場面並沒有出現,只是被當場踢爆不知道該街的街名,枉為樂富老街坊。最搞笑的是,連那保安阿姐被問起街道的名字時,也手忙腳亂了好一陣子。既然有這麼大的一個麥記招牌屹立不倒十多年,還有誰會留意那到處大同小異的街道名牌?不過這應算是另一種悲哀吧。
星期一, 11月 12, 2007
青春的約會

記憶中只有三次學騎單車(只計兩輪)的嘗試。第一次是在嘉湖山莊的公園中,那單車是紅色的,由不知名人士所贈。奇怪的是我完全不記得過程,誰在教我,自己究竟有沒有成功走了一兩步。第二次在宜蘭冬山河親水公園。本打算和貓同學一起在冬山河畔踩單車,又想像自己在入口租車處就可學會,但由於地面上滿是碎石,車子又太高,太怕跌倒擦傷,最後還是輪盡地坐貓同學的車尾,還害她翻車幾次,真是不好意思。第三次也在台灣,是台東市的三隻小豬民宿。民宿免費借出單車,但全部都很高爬不上。作為民宿第一個持外國護照的住客,我受到老闆及其助手熱心的協助。他們雖說教我騎,但其實見到一隻笨拙的動物在沙石上跌跌撞撞,也是相當令人沮喪的。最後雖然也成功騎到一兩米,但這樣子踩出馬路好像更危險,所以還是以11號公車代步。
相對於私家車或單車什麼的,我還是比較喜歡大眾運輸系統,不過也許我必須承認,〈夏天的尾巴〉真的大大激起了學騎單車的決心,哪怕當初入場主要是想看高鐵。所以,在風和日麗的周末,相約政政寡佬六人(我被所有女同學拒絕了,有意參與下次秋季大旅行的女士們請留意下次活動安排!)往大埔墟騎車去。我本來的想像是在大埔墟坐巴士到大尾督,然後在大尾督一帶騎車,但在大埔墟火車站碰面時,講多兩句後又覺得這樣太無聊,所以大伙最後還是在火車站旁的租車店租車。由於要在大尾督還車,連運輸費每人索價五十元。
從富雅花園出發,推車至寶湖一帶,在林村河的單車徑上開始試騎,穿過一個不知名的公共屋村,然後沿著漫長的汀角路到達大尾督。沿途固然盡賞吐露風光,但仍不免跌跌撞撞,很多時候同學說要先取得平衡才會成功,我通常的反應是在心裡爆一句粗,然後說「就是不行」。單車明明就是一些很輕巧(看起來啦)的東西,但一騎上去之後就會覺得整個方向盤(不知如何稱呼)都很重,要出盡力推,它才不會擺來擺去,固定在一個我想要的位置或方向,所以踩畢全程後手腕真是有夠累的。除了平衡之外,我想自己最難克服的是速度。我想自己不是那些能夠駕馭高速的人,所以一下斜坡,單車不由自主的加速,就開始心慌。有時候在應是可以順利飛過的斜坡,我總在中途煞車,硬生生的停下來,差點飛出車。
其實現在想來,我不太知道自己在哪方面出多了力,或者為何突然在途中某處如有神助,能夠克服之前幾次失敗的陰影。也許是車矮了,也許是踩的時間長了,也許是同行者的期望和支持的程度不同了,也許是比以前更好勝了。但是,到真的學會騎的一刻,真想尖叫:「我終於學識!」多謝各方好友不離不棄,令人心酸的穩健友誼又再發威,讓我經過了22年的步行生活,終於趕在青春期就快完結前發現了一種可以自行操縱的代步工具,哪怕後遺症是一些超級老餅的腰痠背痛和手軟腳軟。
算吧,我們真的不小了。
星期五, 11月 09, 2007
論文心情(持續更新)

什麼時候我覺得論文寫來寫去寫不完:
連續七日睡至午後才醒來;整天都在看youtube;突然上不到網;因為生理關係終日眼訓;檯面上的紙散落地面,又不小心被踩了腳印;看到旅遊網站很想去旅行;肚餓到什麼也吃不下;交功課前夕還是提不起勁寫;去完組聚之後大家都在談工作,學校的事已沒有人感興趣;一整個月的時間表都是空白的,然後發現今日才只是九號;圖書館傳來連環催還電郵,但那書完全未看過;老細說我的文字(暫時真的只是文字,我估)寫得不好;老細的樣子看起來欲言又止奸到出汁;失戀(不是無痛那種);老媽子催回家吃飯
什麼時候我覺得突然很有衝勁寫論文:
去完很柒的seminar;突然很想讀博;聽到關於一些別人的無聊研究的事;看到一份很想做的工的招聘廣告;想像寫完可以去一個月的大冒險;見完點條明路我行的老細;聽到與「準時」和「畢業」有關的字眼;難得地在參考書上看到爆笑的事情;發現自己終於看得懂政府統計數字(花了好大的勁);收拾好桌面,不論是書桌還是電腦的桌面;洗乾淨了三四天前喝完咖啡沒洗的杯;淋花;看到研究所求生手冊中他人的慘況,然後覺得這些不會發生在我身上;覺得自己不應再對undergrad產生太多認同感和留戀
星期四, 11月 08, 2007
愛之流刑地(二)
冬香被殺後,村尾在第一次口供的時候強調,因為自己愛冬香,所以才想完成她的願望,也就是被他殺死。他一直認為,自己會捨得殺死冬香,是因為太愛冬香。他以為自己和冬香的想法一樣,而他也成全了她,所以不論警察如何描述他為了掩飾這段不倫關係而行兇,他也全盤否定。
然後檢察官織部接手調查,在面談之中,村尾回憶起他與冬香相遇的經過。
村尾和冬香相識於村尾失意之時──他是愛情小說家,久未發市,雖然在大學裡還有教席,也定期為雜誌社供稿,但他還是覺得自己已失去了創作力,甚至乎,失去了寫作的熱情。以前的編輯朋友為了鼓勵他,便介紹了一位書迷給他。
那就是冬香,已婚,有三個小孩,自十八歲起就把村尾的《戀愛的墓碑》反覆翻看。該書的女主角不斷以玩弄男人為樂,最後自我了斷。冬香折服於女主角的妖豔、自由、個性,但她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有如女主角般的勇氣。
後來,村尾覺得自己與冬香墮入愛河,寫作的動力又回來了,要以男人遠遠追不上的女人的熱情為題,再寫一本書。隨著對冬香的熱情一發不可發拾,他也不斷的寫著名為《虛無與熱情》的新書,並要冬香成為第一個讀者。在小酒吧裡,雜誌社的編輯說,戀愛是唯一可與寫作並存的東西,那時村尾低頭一笑,想來是覺得如魚得水了。
村尾的女兒高子,對《戀愛的墓碑》的理解與冬香的一樣嗎?與女主角同齡的高子認為,《戀》的女主角每天在遊戲人間,有一天突然間忍受不了痛苦和罪惡感,所以選擇死去。高子認為,冬香沒有勇氣自行了斷,需要一個願意殺死她的人,所以才請求村尾把她殺死。冬香本來就有被殺的願望,所以村尾只是被利用了,並沒有錯。
村尾又回憶起,冬香曾說,請他殺死她,她不想自己死。
然後檢察官織部接手調查,在面談之中,村尾回憶起他與冬香相遇的經過。
村尾和冬香相識於村尾失意之時──他是愛情小說家,久未發市,雖然在大學裡還有教席,也定期為雜誌社供稿,但他還是覺得自己已失去了創作力,甚至乎,失去了寫作的熱情。以前的編輯朋友為了鼓勵他,便介紹了一位書迷給他。
那就是冬香,已婚,有三個小孩,自十八歲起就把村尾的《戀愛的墓碑》反覆翻看。該書的女主角不斷以玩弄男人為樂,最後自我了斷。冬香折服於女主角的妖豔、自由、個性,但她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有如女主角般的勇氣。
後來,村尾覺得自己與冬香墮入愛河,寫作的動力又回來了,要以男人遠遠追不上的女人的熱情為題,再寫一本書。隨著對冬香的熱情一發不可發拾,他也不斷的寫著名為《虛無與熱情》的新書,並要冬香成為第一個讀者。在小酒吧裡,雜誌社的編輯說,戀愛是唯一可與寫作並存的東西,那時村尾低頭一笑,想來是覺得如魚得水了。
村尾的女兒高子,對《戀愛的墓碑》的理解與冬香的一樣嗎?與女主角同齡的高子認為,《戀》的女主角每天在遊戲人間,有一天突然間忍受不了痛苦和罪惡感,所以選擇死去。高子認為,冬香沒有勇氣自行了斷,需要一個願意殺死她的人,所以才請求村尾把她殺死。冬香本來就有被殺的願望,所以村尾只是被利用了,並沒有錯。
村尾又回憶起,冬香曾說,請他殺死她,她不想自己死。
星期五, 11月 02, 2007
星期四, 11月 01, 2007
蒙馬特遺書
訂閱:
留言 (Atom)